西峰区图书馆丨【嘉宾导读】丨家在中村(李安平)
在宁县的最南端有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,她像一个向南倾斜的簸箕,塬、沟、川交错,煤炭、石油储量丰富,海拔只有800多米,南接陕西长武,东连正宁榆林子,西临长庆桥,泾河、马莲河在此交汇,土地肥沃,雨水丰沛,气候适宜,人口有四万多众,是庆阳著名的文化之乡、长寿之乡和苹果之乡。
中村原名坳里,有平坳大原之意,是庆阳市土地最肥沃的地方,土壤是清一色的黑垆土,面积达160平方里,耕地面积8万余亩,有18个行政村,是庆阳著名的产粮大镇。低位的海拔和向南倾斜的地势赋予了这块土地足够的阳光和雨露,这里的庄稼因老天爷的护佑见年都是大产,只要你肯撒一把籽种就会有收成,土地绝不亏欠勤劳的中村人。这一方水土主产冬小麦、玉米、油菜、大豆等作物。当然从老百姓内心来说,还是偏爱小麦的。农民的一年光景全押在地里的小麦上,“麦子一黄,绣女下床”,只要到了麦子收割的季节,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会忙乎起来。端午前后,夏至到了,麦子不长了,熟了。麦子熟的时候,布谷鸟就会“布谷,布谷”地在村里鸣叫,催人下地。政平和白马庙、车家坪川道里的麦子先黄先割,其次是沟里洼里的麦子搭镰,最后才能轮到满坳塬上的麦子抢收。中村人爱囤积粮食,家家都有余粮,既是囤里麦子冒尖,多出来的粮食也不糟蹋,不轻易粜。老一辈人最见不得年轻人糟蹋粮食。用中村人的话说,惜粮就是惜命。
中村有着丰富的人文传说。著名的赵匡胤访苗先生的传说就发生在此地的封侯村,传说,宋代名臣苗存义帮宋朝打下江山后归隐回乡,赵匡胤不知所踪,便来宁州访贤,寻找苗先生的下落。到了宁州,听说苗先生在院子村,骑马过桥时坐骑的金玲丢失,苗先生也没有找到,赵匡胤便将此桥赐名“金铃桥”。赵匡胤求贤心切,一路快马加鞭追到遇村,终于见到了苗先生,君臣二人说说笑笑,一路来到苗先生故里。一番寒暄之后,赵匡胤欲让苗先生出山辅佐宋室江山,然而,苗先生誓不相从,赵匡胤只好作罢。为了感念苗先生功德,遂将先生所居之村赐名为“封侯村”。
“三江口,红花驿”的来历就更为奇特,古代政平有个人在朝廷为官,受到了贬谪,皇上念起平日有功,问他愿意贬到何处?他实际上想回乡,怕圣上不准,便机智地答道:“臣愿贬往‘三江口,红花驿’”,皇上不明真相,便恩准了。他便如其所愿地回到了家乡政平。
白马庙的传说有两个版本,一则说,明代名将常遇春在此征战,所骑白马留下了一个硕大的马蹄印,后人为了纪念常遇春和大白马,在此地建了一座白马庙;另一则说,古代发洪水,一个儿童被大水卷走,危急关头一匹大白马凌空而下,将孩童救上岸,随后遁入天幕,乡民直呼:神马下凡。遂建白马庙,纪念神马。传说归传说,白马庙至今庙宇尚在,香火犹盛;神湫依存,据说,湫水可明目,四里八村的民众常用瓶子灌此水洗目,似有奇效。
中村大的庙会有三个,说是庙会,其实也没有啥宗教成分,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,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,到了农闲的季节,就以祭拜神灵的名义,自发地过个节日,既能求个心安理得,活跃一下沉闷的乡村气氛,也不显得奢侈。政平“三月三”庙会动静最大,正会那一天,惊动陕甘两省三县民众,一时政平川道人流如织、摩肩接踵,摆吃食摊子的,卖衣服的,卖娃娃玩具的,套圈圈的,摇麻糖会的,耍杂技的,惹逗的人心浮动。戏台下、庙院里只是些年龄偏大的老汉老婆婆,年轻人都四处看热闹去了,看戏拜神似乎只是个幌子;中村村“三月十八”庙会由本村村民发起,拉动全镇民众围观,会期一般三到五天。中村人看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,群众都是精明的鉴赏家,一个唱腔一个动作细品,甚至连武生翻跟头、马夫轮鞭子也要点评一番,着实不好糊弄。演员若是不明就里,一味敷衍,观众不但喝倒彩,还往舞台上丢砖头呢。看戏的挑剔,当地戏入不了老百姓的法眼,组织唱戏的会首也是战战兢兢,只好花大价钱请正宗的陕西戏班子助兴,方肯作罢;以西王为中心的周边村子信奉地方神灵“杨四爷”,香火不断,庙宇坐落在西王村口,异常壮观,每年四月八轮流坐庄,民俗味浓厚,常有“马角”显异。这几个村子对戏的瞎好不太讲究,只图有个氛围,自乐班子也行。他们看中的是抬神、敬神、代角子的细节和民众的参与程度,敬神用的水要挑选精壮的小伙子跑步下沟到水泉上接,然后,一路狂奔,到达庙院,沿途老小一律让路,不可阻拦。正会那一天,全村忙碌,能干的媳妇要做名目繁多的祭品,纸活匠还要做挂蜡的花圈,小伙子要把正殿里的轿子擦洗干净,披上红布,绑上抬杆。祭拜仪式一开始,会首和长辈跪在神像前上香表,其他人跟在后面磕头。抬轿的是四个精壮小伙子,神灵一旦“附”了体,轿子就左右摇晃,四个小伙子都列不住。最惊心动魄的是“代角子”,眼看着扮演“角子”的汉子一副病殃殃的样子,霎时如同得了神力,碗口壮的麻鞭轮得飞舞,发出“啪,啪”的脆响,人群惊开一个圆场,娃娃吓得魂飞魄散,四处躲藏。“角子”的扮演者对着正殿,“嗖,嗖,嗖”连翻三个跟头,倒地扯成硬棍,看得人目瞪口呆。少时,“角子”翻起身,全身像索绫一样颤抖不停,嘴里一串四六句子,念念有词,叫人似懂非懂。这时,会首代传神语,“明年玉米成了”,如此云云。民众听到“明年玉米成了”,一阵喝彩,顿时掌声雷动,鞭炮、乐鼓齐名,舞台上的戏子也来开了唱腔,一时庙会热闹达到极致。中村村的老中学原是一座庙院,叫“中原寺”,解放前寺里有和尚,寺内有一棵大槐树,粗有数围,少林寺《中国古树名录》有记载,七八个小伙子围不住,毁于社教。大槐树被伐后,树盘鸟粪达尺余,乌鸦哀鸣连罩数日不散,南北胡洞的村民仅树根家家门前都垒了一个硬柴垛。旧社会,中村镇许多村子都出过贡生,朝廷在祠堂立过铁旗杆,可惜都毁于社教和“文革”。
早在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,镇内的白马庙、十二盘山、车家坪曾出土过珍贵的陶器。在唐代,政平村就设县,至今尚有唐塔、张家书房、堡子山等文物遗迹。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遗存留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崇尚文化、重视教育的风气。中村的村落基本上以一村一姓群居,井然有序,辈分清楚。比如,弥家村、西王村、乔家村、郑家村、刘家村、李家坳等等。有些村子也有杂姓,但是不多,他们和村里的大姓几乎都沾亲带故,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辈分上也能说个所以然。这种大姓为主导的村落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定的村风和家族文化,人心也齐,只要有能人引导,大家都看样样,你弄啥我弄啥,不知不觉就成了气候。有的村出木匠,有的村出铁匠,有的村出识文子,有的村出司机、有的村出工头,有的村出大学生,综合起来来看,村村都有特点。中村人爱耍社火,大户曹家的柳木腿最富盛名,是县上的非遗传承项目;苏韩村的舞狮源远流长;西王村的车故事颇为考究;中村村的的故事有很强的神话色彩;孙安村的灯故事荡气回肠。中村的文化村很多,随便出来一个老农民你也不敢轻视,开口不露白,肚子里都有些文墨,四六句子张嘴就来,不是识文断字,就是妙解戏文、善讲故经,甚至提笔舞墨挥洒丹青,也不在话下。大户曹家是出文人墨客的名村,晚清时期一笔好写的曹平江做过河南偃师县长,口碑至今犹存;贡生曹应辰赴西安榛荟剧社打戏,其作《顶灯记》《软玉屏》《女灵》《夺锦楼》唱彻西北五省;现代书画大家曹芝川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,也是名震一方的书画家,其欧楷功力深厚,兰草芦雁神采飞扬;陇上乡贤安逸民是现代农业水利专家,曾获五一劳动奖;当代名医曹艾生精通岐黄之术,远近闻名。老话说得好,“下了政平坡,先生比驴多”(这话可不是骂人的话),建国后省文联副主席、《红旗手》杂志主编、全国著名作家李秀峰就是政平人,村里至今还流传着“秀峰爷”少年勤学的故事。还有名冠一时的张家书房,都是出先生的实证。像乔家、刘家、郑家、西王都是先生扎堆的地方,不容小觑。大集体时,中村曾分为中村、秦村、新城三个公社,同时,还设有两个初中和一个完中。后来,分分合合,变成中村乡和新城乡,最后又合成如今的中村镇。中学也发生了变化,完中撤了,变为三个初中。临近中村的宁县一中,几十年来,有近乎一半的优等生都是来自中村,他们在这里写下了许多感人的勤学故事,由此走向了地北天南,刷写了无数的人生记录。
中村人个性耿直,稍带倔强,为人正派,出文化人,也出政府官员。中村是全县著名的文化之乡,各种文化人才层出不穷。著名诗词家乔曰麟,诗词意境幽深,功力深厚,可惜“文革”末期自尽,遗作被其侄子乔孝堂编辑成《乔曰麟诗集》出版。群众亘古注重书画,写字画画的人也多,许多村民家里都爱挂字画。中村境内能叫上名号的书画家不下百人,今人名家众多,省城有名的省书协副主席刘满才行书秀雅洒脱,书画俱佳的市书协原主席安石书法俊美、鹰画兼工带写甚为传神,陕西著名书画家、咸阳美协副主席韩英海山水画气势磅礴,全市闻名的书画家曹筠生线条老道、风格独特,蛰居宁夏的书画家郑少白人物画线条洗练、形神兼备,远在三原县的书画家李聪虎牡丹栩栩如生,深得本地人喜爱的书画家杨复兴善书何绍基体小楷,在本市和其他地方工作的书画家张鹏程、张鹏英、安贞、曹维祥、郑青斌、李贵升、李景红、李晓琳、郑小宁、曹达理、李清舟、张明新、郑克峰、张旭、张萍、李进儒、曹维军、曹治军、刘小平、安锋、郝书学、郑振东、刘文龙、郑开运、李高、王燕春、李蕊、李缇、李浩然等数十人亦是各具特色。已故书画名家曹芝川、王政学、王春和、赵连升、周德考、罗俊吉、李红锐、曹艾生作品流传甚广。民间老画匠王子钰父子两代善画庙宇神像,足迹遍布陕甘宁周边。大户曹家还成立了凤尾山书画社,刘家村办过大型的书画笔会,中村村上也搞过书画展,热衷于书画收藏的人更是不胜枚举。别看中村是乡下,有人还是朗诵播音的国手呢!弥家村的弥亚牛靠着自己的硬实力,从一个县上的播音员,一直干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频道的主持人,他的富有磁性和穿透力的声音早已传遍了世界各地。摄影家乔旺堂是庆阳摄影界的泰斗,用相机记录了庆阳几十年的珍贵历史瞬间。音乐戏剧名家也是人才济济,有被周总理接见过的二胡演奏家张美玲,县剧团板胡领衔演奏家姜正德、李选伟,闻名陕甘两省的秦腔丑角赵志明。八十年代,中村村人赵连升当过地区专员,为官十分清廉,中村至早胜路面坑坑洼洼,县上和地区交通部门准备铺柏油路,他在大会上拍了桌子,“我个人不能搞特殊化,全区路面铺不完,我的家乡就绝不能铺!”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了400棵松树苗赠送给中村小学,希望小学生像松树一样茁壮成长,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老专员已作故多年,其官声在民间传颂。九十年代,中村有八大处长,个个都手握实权,在当地影响很大,可是他们都不扎眼,不抱团、不营私,本本分分地为老百姓服务,为家乡赢得了好名声。
中村人长寿的多,是全市著名的长寿乡,俭底村是全市长寿人数最多的村子。八九十岁的老人村村比比皆是。老年人日复一日,过着不紧不慢的生活,春天在地里除草,冬天在阳面晒暖暖,日子过得惬意着呢。中村人长寿一则是地理位置优越,地形向阳,气候冷凉适中,空气中负氧离子高,天蓝气清;二则是中村人生活节奏慢,容易知足,人老几辈崇尚节俭;三则是年轻人爱老、敬老,不多嫌老人,老人也德行,不给娃娃添乱。老人是个宝,是一个家庭的灵魂,没了老人,日子立时寡淡无味。老年人节俭,即使再有钱也不得大手大脚,奢侈浪费,否则,众人都骂哩。娃娃在外面打拼,挣了钱就往家里寄,老人也不乱花,一分一分地攒下,零地存成整地,一恍惚,就把日子过下了。中村农行和信用社的存款在全市都是前几位。
也许有人说,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老皇历了,如今的中村早已今非昔比了。嗯,谁说不是呢。
这些年,中村和庆阳许多地方一样,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老专员的话早就变成了现实,中村到早胜的公路早铺了,中村到长武的路也铺了,中村到长庆桥的路也铺了,中村到榆林子的路也铺了,村与村之间的路也铺了。甘肃最大的煤矿榆林子煤矿横跨榆林子和政平,隆隆的钻机从地下没日没夜地挖着乌黑的煤炭;面积达两万亩的正阳果业园把中村、平定、西王、刘家几个村都连成了大花园,成了4A级风景区,盛大的苹果节和马拉松比赛每年五月都会如期举行;长庆油田的钻井队和抽油机已在平畴千野的中村落户生根;适合农村发展的现代养殖和种植业已让许多农户尝到了甜头;剩余的劳动力早已蜂涌到城里打工、创业,过上了现代化的新生活;从中村走出去的莘莘学子、适龄军人也洒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,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。
对于每一个中村人来说,无论身在何处游荡,依然心系家乡,在现实和梦境里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赋予过自己生命的故土。年年苜蓿发芽的春天,桃花盛开的季节,麦子拔节的清晨,苹果花开的芳菲五月,那些远离中村的游子都会在心里眺望着如诗如画的家乡,默默守护着日夜萦绕的灵魂家园,和这方土地一起发芽、生长、开花,播撒生活的希望,收获耕耘的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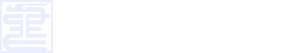

账号+密码登录
手机+密码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