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峰区图书馆丨【嘉宾导读】湛蓝之城(杨永康)
通红蒙语怎么说呢?
苏干又使劲地搓起自己的手来。他的手越发红了。
我安慰他说,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一点点抵达它的深处,它巨大的深处,它很难走到尽头的深处,我们已经听到其根茎间发出的细微碎裂声。我们都下意识地收紧自己的衣袖与袍子,还有腿,以减少撕扯与摩擦,荒草正一点点没过马的膝、我的膝。
我感觉在碎裂声间穿行的不是我,也不是苏干,也不是马,而是他浅黑色的靴子。我们都下意识地弯曲着,极轻微地弯曲着,像那些不断出现的细微碎裂声。只管随它前行就是了,偶尔有什么野物被我们惊扰,我感觉是一只兔子,苏干说是沙狐。沙狐不就是藏狐吗?苏干笑了笑说,沙狐不是藏狐。我们还碰到一堆灰白色的鸟蛋,苏干说是毛腿沙鸡的蛋。我见过沙鸡的画片,羽毛的色彩很是斑斓。
然后就听到水声了,我们都有点激动。特别是苏干的马,对着我嘶鸣了好几次。苏干说前面就是沙拉果勒,应该是疏勒河以南最大的一条河。横在我们面前的河并不宽阔,像一条可以随风摆动的小丝带。苏干说,再靠近点就能体会到它的威力。再近出现很大的一片赤褐色的沼泽,重度的赤褐色一直延展至遥远的雪峰下。苏干让我闭着眼睛走在上面,真正走上去感觉很是特别,好似在蹈虚一般,没有任何声音。苏干时不时回过头来喊我小心小心,别陷进沼泽里,我的一只脚还是陷进去了。不过并不影响继续前行,只是鞋子里不时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。
再走一程,沼泽中出现一个灰色的山包来。确实是灰色的。看起来并不很高,爬起来并不低。苏干先上去的,然后从马背上取出一双靴子,一双蒙式皮靴,上面有乌林赫纹与乌历吉赫纹,也就是云纹与吉祥纹。出发前苏干提醒过我的,最好穿他准备好的蒙式靴子。我觉得太重,行走起来很不方便,没有穿。脱掉鞋子我才感到脚有点麻木了。十一月的沙拉果勒河谷已经很冷,即便在正午也可看到草尖上白白的霜粒。其实我的脚在水中“浸泡”最多只有几分钟时间。苏干说,一小会儿就足以腐蚀掉一个人的脚指头,水中的含碱量太高。
苏干一边唠叨,一边从马背上取下一块带毛的皮子来,让我先在皮子上暖暖脚,由他处理我鞋子中的水。应该是沙狐的皮,我闻见了一些气味。我与苏干讨论过沙狐是否有气味的问题,苏干说沙狐绝对没有气味。我说,既是狐怎么能没有狐的气味?他说也许有,只是被无边的荒漠给稀释了。
苏干并没有从鞋子中倒出多少水来。清理完了水渍,苏干找来一些草的茎秆塞进我的鞋子,他说这个绝对管用,可以保暖,也不容易伤脚。
折腾了大半天,喝了几口苏干带来的土酒,身子一下暖和了起来。定定神看过去,原来沙拉果勒河就在脚下。在一望无际的赤褐色中,银灰色的沙拉果勒河绕过山包在不远处分出几个青灰色的小岔。要不是这几个小岔,你根本感觉不出它的流动。有一个小岔正好从山包一旁流过,泛着青灰色的光。青灰色的光在一片低洼处又分出几个灰黑色的小岔来,灰黑色小岔一直延伸到赤红色的极深处,形成一汪碧绿的小泉。小泉又分岔出几个更碧绿的小岔,起伏到更深。然后出现一些似乎是静止不动的黑色小点,很零散地分布着。应该是蒙古马吧?我问苏干。苏干看了看远处说是驴群,藏野驴。也有可能是野狼群,群狼常穿过黑达坂、克克逊达坂出来觅食。
要是能再靠近点就好了?
没法靠得更近了。除非蹚过河去。
不远处有一个灰色的木头架子,应该是一座简易的木头桥墩。看得出是一座桥墩,顶端有一根很细的木头,应该是桥面。再远一点是一个只剩下半截的木架子。若要蹚过河去,有一个问题要面对,就是怎么抵达那个兀立在河中央、一人多高的木架子。正值枯水期,骑马过去不成问题,问题是到达第一个木架子后怎么跨越到第二个木架子。第二个木架子已经散架,只有两根发黑的木桩一高一矮兀立在水中。根据露出水面的部分判断,是河水最深的部分。应该高过一匹马。要骑马过去,只有一种可能,就是到河心后,想办法让马打一个立挺,立挺的时间要足以保证马上的人瞬间跃过马背,顺利越过两截灰黑色木桩,奋力一跃到对岸。一个环节做不到位,很可能就跌落在水中,后果可想而知。
苏干琢磨了一遍,感觉他过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,问题大的是我。苏干想出一个相对万全的办法来,把他的牛皮马鞍绑在我的身上,是典型的“尖脑大尾式”蒙古族马鞍,标准叫法是尖脑大尾式包股子皮白铜烧蓝福寿纹马鞍,主要由一张很大的褐色牛皮组成,上面有暗灰色的花纹,重量应该有几十斤。重是重了点,但毕竟过河安全系数增加了。苏干的考虑是,即便我真的掉落下去了,皮子正好可以作为铠甲保护我一下,至少不那么容易被木桩刺穿。没有更好的办法了,我接受了这个方案。
苏干先过了河,然后是我。至于苏干的马,一直是跟着苏干,过到一半,正好被什么东西弄伤了蹄子,一下子跪在了水中,水很快就没过了马的嘴与鼻子。苏干有点急了,只好重新返回河的这一边。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马拖回到河的这一侧。好在不是铁钉,是一根小小的木头刺,这意外是我与苏干都没有想到的。苏干说拔出木刺就没事了,好像在安慰我又好像在安慰他的马。
在河的这一边走不久出现一大片白色的盐碱滩。因为盐碱的含量高,赤褐色变成了灰白色与白色,草也变得稀稀疏疏的。不过开始有人类的遗迹了,比如一溜残缺的土墙,还有断断续续的木头围栏。我疑心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座城的残留。我和苏干都上前反复打量了,从土质看应该是后来夯筑的,很不结实,苏干用马鞭轻轻撬了一下就落下一大块松散的土块来。
再往前是一片灰黑色的荒漠,满眼都是灰灰的荒漠植物。比如木地肤、盐爪爪。苏干是这么说的。我感觉后一种像盐生木,或者红砂,即琵琶柴,哈萨克语叫肉木热亚。在荒漠戈壁小蓬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小蓬是一种超旱生柴类垫状半灌木。有一大群羊在这些植物间专注觅食,真有点不可思议,它们吃什么呢?就吃这种发红发灰的草吗?苏干说就吃着种草,当然还有其他草。
可以近距离看看吗?
可以。只是得准备足够的石头,防止野狼袭击。
有野狼吗?
不是有野狼,而是有野狼群,它们就在羊群周围逡巡。一般有牧羊犬看护,野狼没有多少下手机会。
我让苏干待在原地,顺便查看一下马受伤的蹄子,我呢带了足够多的石头。
顺便说一下,沙拉果勒河谷的石头都露在外面,因为沙拉果勒河到这里只剩下一道灰灰的沙石滩了。那些石头就裸露在沙灰中,青灰色的居多。有一块石头看起来布满花纹,圆圆的,捡起来擦拭掉上面的沙土,几道类似人类心脏血管的纹路显现了出来。太像人类的心脏了,着实吓我一跳。越看越像,装在口袋里心里不踏实,最后还是恭恭敬敬放回到了原地。我曾咨询过一位地质学家,石头的花纹是怎么形成的,地质学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我还在沙灰间看见了一些类似干柴的植物,说是植物,更像干柴,有粗壮的根,有很细的枝条,枝条上有红色的花瓣。我仔细看过其裸露在外面的根,感觉很像棕榈类植物的根,有很粗的纤维,呈螺旋状反转着。有一株枝干扭曲得很厉害,呈纯灰色,极像燃烧着的灰色火焰。
正观察呢,一阵急促的呼吸声从对面传来。一抬头,我发现一只“野物”在对面死盯着我看。应该是死盯着我看。临出发苏干告诉过我,牧羊犬眼光里很少有残忍的东西,野狼不同,毛竖立着,牙齿外露,眼露凶光。我的手就在口袋里紧握着一块浑圆的石头,只是一时没法判断对面死盯着我看的是牧羊犬还是野狼。对视了一会儿,那野物退回到羊群的一侧。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,应该是一只牧羊犬。狼的尾巴应该是垂在地上的。
狼的尾巴都垂在地上吗?
都垂在地上。
有例外吗?
差不多没有例外。
绝对有例外的,敦煌莫高窟有一幅西魏壁画,画面中狼的肢体匀称而修长,肢体前伸,嘴巴也前伸着,眼睛亮亮的,通体蓝蓝的,一点穷凶极恶的样子也没有。不但一点穷凶极恶的样子也没有,还极具美感呢。
苏干叹了口气说,要真是碰上野狼群,看你还美感不!
我说也是,真算是有惊无险了一回。
其实那会儿,我不用太紧张的,苏干已经从后面骑马赶了过来,估计他注意到我这边的状况了。实际上苏干并没有立即赶过来,而是站在半截灰黑色的墙影下向我招手,好像很激动的样子,手不停在空中挥动。近一些才听清楚他说他有了重大发现,他找到一段残墙,找到残墙不愁找不到村庄,找到村庄不愁找不到古老的城,城总与人分不开的对吧!苏干的判断是对的,前面确实是个古老的村庄,可以看到一垄垄新翻的褐色田垄与灰黄色的田埂。一簇簇浅黄色的草在风中摇曳,顶端是灰白色的,奇异的是向一侧微微倾斜着。
再远一点是几行高大的树,树冠呈灰红色,也向一侧倾斜着,旁边是一个土灰色的院落,院落的土墙很矮,可以看到一大摞青灰色的麦草垛,草垛后面是一把灰色的木梯,木梯后面是一间土坯小屋,小屋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,窗户的外侧是一个很大的土墙豁口。一声吆喝,豁口里“喷涌”而出十几只羊来。一只接一只,先露出一个灰白色的头,再露出小半个身子,再露出整个身子,再抖动一下身上的灰白色,张望一下外面,这才跳出豁口。最后从豁口“喷涌”而出的是一个女子,女子穿深灰色衣服,戴浅紫色的头巾,跳出豁口之后,羊们早已咩咩着冲出很远。
女子与羊群消失之后,一条石砌的“小巷”出现了,石头形状不很规则,颜色有青灰色的,也有灰红色的,灰白色的,整体看起来是灰色的。顶端是一个更大的麦草垛,向一侧歪着,一根很粗的木头斜倚在草垛上,很粗的枝伸向空中。巷子另一侧是一辆只有一个轮子的蓝色汽车。
再往里是一面土墙,我只好退了回来,一直退到草垛的尽头。草垛尽头是一汪很清澈的水。应该是水塘,水面亮亮的。水塘过去是一溜青绿色的树,应该是青杨或者钻天杨,树干是灰白色的,叶子是青绿色的。青杨过去是一片灰灰的柳树,应该是柽柳,叶子细细的。柽柳后面是一头灰黑色的毛驴。毛驴前面走着一位男子,男子穿灰蓝色衣服,戴一顶帽檐很短的灰色布帽。我一直看着男子与他的毛驴走进院子消失在草垛背后。
在墙外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一切。几间很低矮的小土屋,靠外一间有一个方形的小窗,另一侧是一间只有顶子的草棚子,草棚子与土屋间堆着一人多高的灰黄色草垛。
绕过院落再往前是一片沙柳,枝干很是粗壮,有一棵的枝干一直弯曲到地上。沙柳后是一片新翻的灰黑色田垄,里面的土块很干硬的样子,全是被牛羊踩过的脚窝与痕迹。脚窝的尽头是几株浅白色的树,树枝都向一侧倾斜着,应该是常年风太多的缘故吧。我查阅过这里的天气,风的发生率为百分之十七,长此以往,树枝便向一侧倾斜了。
我问苏干,我的推论还符合逻辑吧?
苏干笑着说,太符合逻辑了。
我曾近距离看过一堵孤零零的土墙,上面全是斑斑驳驳的小洞,蜂巢一般。周围是已经塌陷的灰质土。瞧我又生造了一个词。灰质土背后是起起伏伏的丘陵。我曾在此灰质土前沉思了好久,我心中一直在描绘我要找的那座城的模样。历史与现实总有反差的,你认为宏伟的也许只是一个小土疙瘩,你认为是一个小土疙瘩的,也许隐藏了一段很宏大的历史,后人必须接受这个现实,你不能要求历史一直保持本来的样子吧!历史做不到这一点,时光也做不到这一点,能有缘窥见历史的一星半点已经很幸运了。我们只能推测过往,所有的过往。
也许历史只是一种感知而已,就如同我们对一只羊、一头小毛驴的感知。历史应该像它们一样鲜活才对。也许从来没有死去,只是以我们不易觉察的方式鲜活着。我仔细打量过我碰到的一头小毛驴,它确实对我有点陌生,一直定定站在那里,怔怔看着我,揣测着我,就如同我揣测着它与历史的本来模样一样。它们和历史唯一的不同也许是它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影,而历史什么也没有留下。
我也曾碰上过一只羊,本来它在舒坦地吃草。可是我出现了,一个它不能完全确定的影子在它的身后出现了。它完全不用在意那个影子的,可是它还是忍不住扭头看了那影子。那影子一直站在距离它不远的地方。它几次回头都发现它站在那儿,几乎一动不动。它干吗老站在那儿呢?一个影子老站在那儿,太让它难受了。它希望那影子至少应该向前向后或者向任何方向走几步,哪怕是一小步,它心中就释然了。它必须让自己释然。为了释然它只能扭过身子面对那个影子了。侧面太难受了。可是一旦一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另一个,会更难受。好在一阵风来,那影子终于发生了些许的偏移,被一块很大的土墙挡住了。它希望它被遮住,它太讨厌那个一动不动的影子了。看不见了,它的心释然了。
它决定去喝口水,沙拉果勒河谷的风太凌厉了,简直能吹裂一切,包括它的唇,包括那个讨厌的影子。它希望那个讨厌的影子能被风彻底吹裂,然后散了。散之后呢?之后它就想不了那么远了。还是去喝水吧!前面就有一泓清澈的水。它低头的瞬间水中倒映出一个古老的沧桑的影子来,应该是一座城的影子,一种喜悦浮上心头。它已经抢先那个讨厌的影子看到城了,就淹没在那些枯黄色的草里。感觉更像个矮矮的城堡。对,更像城堡。能清晰感觉到它凸起的部分、凹下的部分,还有其正午投下的浓重阴影。甚至还可以看到它正在崩塌的穹顶。应该正在崩塌。一声牛哞之后一切都变了,一切都乱了。
那牛哞声也时断时续传到我的耳朵里。和牛哞比我更喜欢听小麻雀在一株小草上叽叽喳喳地叫。它们就在我的泥窗之外。有时候它们会叽叽喳喳一个上午,特别亲切。有一天那叽叽喳喳声突然停了,我心中正疑惑呢,苏干骑马来了,一脸的春风。苏干已经好些天没有来了。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对那座古老的城保持信心,说着从包中取出两块用布包裹着的东西来。看起来很沉的样子,放在地上发出重重的响声。里面是一块包日陶斯格,应该就是灰砖,至少是看起来是灰砖的一类东西。苏干先取出一块来,让我仔细看看。我仔细看了,确实是一块灰砖,上面雕刻有花纹。共两块,一块是个立体的盆花,构图非常奇异,一枝弯曲下垂的荷花,顶端是一枝如意形的花蕾。或者本身就是如意。另一侧是一片带纹理的叶子,下端是两个更大的叶片,也有清晰的纹理,只是上端不完整了。中间更像一件古老的兵器方天画戟,花盆中有兵器还是罕见的。另一块是花枝喜鹊图案,花枝基本完整,上有喜鹊一只,只是喜鹊的尾部断掉了。嘴巴很厚很长,感觉像非洲某种嘴巴很大的鸟。
关于两块砖雕的风格我查阅过,应该不是蒙式风格,也不是战国商周以来的以装饰为主的汉族雕砖风格。我曾见过两块战国方砖雕刻,整体以对称图案为主,有很浓郁的装饰味。苏干手中的砖雕风格与构图,我反复比对过,极像天津杨柳青砖雕。有一幅天津杨柳青砖雕叫《莲花》,名曰莲花,正中就是莲花、莲叶、莲藕、莲枝,下端是海水样纹理,枝干、叶片都很粗大。我还看到过一幅天津老城罗家大院鸳鸯喜荷券额,风格也基本接近,图中莲叶都很肥大,粗重,都是大叶子大花类型,源头应该是金代砖雕与明代砖雕。
苏干听完咧嘴笑了,说我还算内行。我问灰砖的来源,他说是费了很大的劲从民间找来的,专门让我看的,看后他再还给人家。苏干想以此证明那座古老之城的确凿存在。我说这只是孤例,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。苏干说绝对不是孤例。万一要是孤例呢?苏干看我这样问,有点急了,说除非……故意没有说出他要说的除非。我笑了,他也笑了。我说除非眼见为实是吧?他说我猜得对。他希望我与他去沙拉果勒河谷以南、以北再勘察一番。
沙拉果勒河谷以北是野马河谷,以南是赛什腾河谷与哈勒腾河谷。我说还是去以南吧!但有个条件,条件是我必须自己去。苏干听了很是难过,沉默了大半天,苏干很少沉默的,最后还是深深祝福了我。还特意把他的圆顶帽塞进我手里,是蒙古族陶尔其克圆顶帽,有很大的金色护耳。
翻过沙拉果勒山抵达赛什腾河谷的时候已是黄昏,我的眼睛很快被一片洁净的蓝所吸引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蓝的东西,应该是典型的靛蓝。一直延展到极远处,被天边一望无际的针茅类植物簇拥成金色。应该是一种针茅类植物,与蓝相映衬。我突然陷入一种莫名幸福里。我已经彻底“突破”了苏干。突破了苏干的什么,还是突破了我的什么呢?抑或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,他就是另一个我?我就是另一个他?没必要做这个类比了,我的灵魂已经变得轻盈。而苏干的影子包括脸越来越模糊了。还有他的褐色靴子。我没有想到这模糊来得这么快。我想在日落之前抵达那里。我第一次觉着这才是我这一行最想要到达、最想要历尽千辛万苦的。是的,我必须为我的这一行找到一个理想的归宿与归途。我已经犹豫得太久,我已经无路可走。我想看到这个傍晚最盛大的湛蓝与靛蓝。我希望那蓝色能簇拥我。之外我已经不需要任何簇拥了。
我希望苏干能理解这一切,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。他已经陪我那么久。不久前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,他已经弄清了那座城的古老方位,包括尺寸,其中东墙多少米,西墙多少米,北墙多少米。他特别强调说这都是他历尽千辛万苦搞来的。城门尺寸呢?城门尺寸暂时还没有搞到。他说这只是暂时的,让我放心。他说他已经跑遍整个西祁连与阿尔金山北坡,包括库木塔格沙漠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。他甚至给我展示了他的好几双千疮百孔的靴子,他想要证明他走过的路,及他的重要收获。他再三说这只是他所有重要收获中的“无区肯”,还多次重复了这个词,是蒙古语。他说整个蒙语话语体系中就这个单词对他来说最意义非凡。汉语的意思叫九牛一毛。他希望我相信这一点,就如同相信他的马一样。他说他已经为此废掉了三匹马。
苏干最重要的收获除了他声称的关于那座城的方位与尺寸,还有几座古老的寺院的古老历史。他特意为我提供了它们的名字,比如色尔腾寺,乾隆三十三年的。阿卡堪布寺,同治九年的;乌呼图勒寺,民国五年的;还有扎西彭措寺等等。前面几个都毁掉了。
你说那两块雕砖会不会就来自这些寺院呢?我问苏干。
怎么可能呢?苏干反问道。
我说怎么不可能呢!
感觉未必是砖,很可能是一种墙体建筑材料。
… 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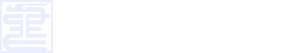

账号+密码登录
手机+密码登录
还没有账号?
立即注册